
|
MoMA原一男回顾展;原一男本人于迈克尔摩尔参加映后讨论,两句话印象深刻:1、原一男:奥奇这个人是个推销员。2、摩尔:奥奇在影片中多次指挥警察指挥摄像机 看起来他也是导演。摩尔这句话引起观众一片哄笑,但却值得深思。一般来讲,一部作者电影往往是导演的意志的体现,即摄像机指挥被摄者。直接电影则谋求摄像机被忽略。而《前进神军》则走得更加极端,摄像机允许被摄者反过来指挥它,也允许被摄者奥奇指挥其他被摄者,奥奇实际上的确行使了部分导演的职责。另有一个花絮:奥奇去杀中队长的时候邀请了原一男去拍摄,并且称这是给原一男的礼物。 |

|
7.0 在审问吃人事件的参与者时,奥崎谦三反复强调摄影机的存在,摄影机这个隐性的暴力机器成为他争议行为的靠山;掌握着摄影机的导演知道自己有了类似于“史官”的特权。但同时,摄影机也在无形中审问奥崎谦三。这种审问态度是拿摄影机做纪录时必然存在的一种“理性”,并不随导演对奥崎的复杂情感而改变。因此整个电影一直在“对奥崎的情感—对战争的立场—摄影机的理性”交织的网格中进行 |

|
以前不明白英译名为何是“The Emperor's Naked Army”,原来化用自安徒生《皇帝的新装》,奥崎所做的就是揭穿谎言和寻找真相。与其说是客观的纪录片,不如说摄影机的在场更给了奥崎勇气甚至是“表演”的动力。原一男访谈里交代了很多细节:当年奥崎由于被盟军俘虏,没看到战友相残的过程。新几内亚的素材被没收是因为没有拍摄许可。奥崎虽然疯狂,但不疯狂就无法在独自对抗权势的过程中取胜…… |

|
高铁上看完。感慨持续愤怒是一种最需要勇气和毅力的能力。因为总有一些人在人们口口声声“谁都有追求平静生活的权利”时,仍在为罪恶为不公为该赎罪的人连说出真相的忏悔都没有而持续愤怒,人们不那么容易遗忘,再犯一遍错的时间也得以被推迟。复杂的点在于,奥崎仍是以暴力威逼的方式,迫使那些老兵直面过去。他说如果目的正确,那么暴力是可以允许的。但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目的,谁又掌握阐释的权利呢?奥崎的一面是痛苦的悔罪者,另一面则永远是曾杀戮甚至食人的幽灵。 |

|
1. 这个男人了不起啊,求真,并且有行动,不怕承担责任。还有特别执着。2. 其实那些杀人犯除了最后一个,其实最有悔意的,反而一身病,物质条件也一般,其他人活的都很好,那个发出命令的长官活的最好,经济条件优渥。3.男主了不起的地方,还在于他直指天皇,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敢这样。 |

|
“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救救狗日的…——狂人日记。企画:今村娼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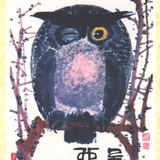
|
"If the result is good, violence is justified." But that's exactly why Japan fought the war |

|
纽约威廉斯堡的超小型地下影院放这个,之前的预告片也是好可怕的录像带画质超low的B级cult片,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么说吧,一个纪录片,到最后采访者和被采访的打起来了,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执拗的男主简直是凶残啊!看到最后发现企划是今村昌平!于是一切都有了解释。。 |

|
奥崎谦三击打被访问者的行为、人格特质、对暴力和天皇的看法值得观察。日军在新几内亚似吃“黑猪”“白猪”的行为在之前1972年《飘舞的军旗下》也有涉及,但这部里某些受访者笑眯眯、平静地说出这些,比直观展示“肉”的影像更具冲击。被访问者的话术与表现非常典型,说谎、否认、撇清自己的责任,例如说自己只是下令但没动手、不在场,说是战争和日军制度造成恶果而自己只是服从命令,把说出真相会伤害活着的人当作说谎借口且指责试图找出真相者是令死者无法安息,指责被非法处死者本身存在问题,事后追问没有意义等等说辞,对日本的其他现实事件来说也常见。假扮身份的访问者对纪录片这题材来说也有意思。 |

|
奥崎用罪与罚式的癫狂忏悔自己的罪,活着回来的人都背了自己的十字架。而软弱的大多数异口同声“每个人想法不同”,安安静静苟且偷生。当然日本的二战反思不足很大程度是外力原因,而内在正是这样的精神疲弱,需要被点明被刺痛。 |

|
奥崎谦三,曾经的二战日军士兵,坚定的天皇反对者(天皇应为战争负责),追问战争真相的偏执狂。他以不恰当的方式(极端行为、暴力)为死难者招魂,但是,当当事人故意满嘴跑火车的时候,何为恰当的方式? |

|
奧崎謙三認為可以尋找到真相的暴力也是正當和合適的,所以他就一直孜孜不倦去尋找「國賊」被處決的真相,哪怕是窮盡了一切。原一男的鏡頭介入顯得平和又唐突,然而又沒有渡邊文樹的那種粗暴。要是奧崎謙三當年遇上渡邊文樹或許會是相當的過激(當然是癡人夢話)。 |

|
4.5,Post-War的伦理责任问题,“神军”是对于皇军的反讽,穿越日本重建证据的过程是死者幽灵在日式空间之中的返魂/复仇。纪录片是对于私密空间的有意闯入,摄影机对于人物面孔,言语以及奥崎谦三语无伦次状态的凝视则是暴力的,令不可纪录的战争显现。他的拜访总是以日本人最熟悉的鞠躬,寒暄开始,但这种礼节仪式并非指向小津之“空”而是强度,一种令文本本身不再重要的强度,在奥崎的卡利斯玛中,原一男保持冷静凝视的摄影机开始直接参与叙事强度,具体表现在一阵强烈的躁动之中,最终在对方失禁的身体中产生触觉。所以奥崎谦三和他夫人口中的“天罚”是什么?它是一种犹太化的神道教救赎观念,破坏了万物有灵论/英灵与作为“人间神=政治神学”的天皇的意识形态装置,一种高桥哲哉主义。 |

|
從尬笑到談笑風生,一直到隨口就是拿「拍你喔」作為威脅受訪者的口實,奥崎謙三對攝影機「在場」的理解實在近乎本能…….這樣一想,倆位死者家屬的中途脫隊,理由就值得玩味了。是不是他倆感覺,奥崎的表演慾註定會讓這趟追尋流入失焦無力?還是單純察覺奥崎的目的後,絲毫不想成為永留銀幕的共犯? |

|
奥崎意识到日本的本土宗教从未完整地破茧,天皇即使在君主立宪之后仍然作为权能-暴力的最高显现被赋予图腾学的意涵。塞尔托说,历史并非总是确定无疑的。士兵们选择闭口不言是因为他们深知他们有权构造历史,他们并非拒绝再现暴力而是拒绝唤起暴力,这种暴力潜伏于日常,甚至遍布整部影像。他们选择性的无视、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欺瞒恰恰确证了它确凿而根深蒂固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奥崎说“战争还在继续”。奥崎以一种激烈的、诉诸身体的精神助产术完成了一场必要的密仪。 |

|
导演除了放大一些细节基本毫无干预,而设计「台词」、选择演员,甚至利用摄像机去表达、干预的,都是奥崎本人。这就让这部「纪录片」变得难以复制的奇异。一遍一遍平铺直叙的采访的重复,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而奥崎时不时对于拍摄的提示,又让人不断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反复的跳脱沉浸焦躁和怀疑中,我们似乎触碰到了一点点残忍的真相,却也毫无立场去指责那些吞吞吐吐或者卖力「表演」的任何一个人,甚至也无法评论拍摄行为本身,因为见过地狱的不是我们。感谢大荧幕让我能够沉浸地看完了全片,虽然中间一度很想逃跑。4 |

|
最早听说这个片子是在纪录片《电影史话》里,一部创新纪录片技法与风格的伟大作品。看的过程中几次惊呼,奥崎谦三的偏执与导演创作上的执着构成一种文本意义以外的互文。(想到一会就要见到原一男导演了,内心还有些激动。) |

|
奥崎谦三是一个从战争丛林中走出来的幽灵,他缠绕着那些想遗忘的当事人,也拍击着一个逐渐淡忘历史的国家麻木的灵魂,那一场场的“拜访”逐渐拼凑出残忍的真相,逼仄的和室内压抑的气氛,如一个道德的法庭,奥崎挥舞着他残缺的手掌,质问着那些军官,甚至不惜诉诸暴力,也要让他们亲口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道歉,原一男和今村昌平巧妙地隐藏了自己,但又无时不在提醒着观众他们的在场,在昭和年代逐渐落下大幕之时,奥崎谦三却固执地要揭开它最黑暗的一角,所谓的圣战和国家荣誉在人性的深渊面前也显得如此地可笑和虚伪,另一方面,这种迟来的“审判”不也正印证着日本战争责任的推诿和淡忘?作为“秘密”被小心守护着,天皇仍然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他没有道歉,也不会道歉,时至今日,那肮脏的血液还在这里流淌着 |

|
偏执狂对偏执狂 |

|
今村昌平流的纪录片,镜头几乎不持立场(如果有就是对反思,对纪录行为本身的同意)。包括主角在内,没有一人的态度不需要怀疑地审视。侵略的战败方的复杂程度远比想象的高,以至于他们如今无论作何姿态,对于被侵略者而言,都不会是合适的。 |

|
8.5/10。影片受访主人公奥崎谦三,二战日本前士兵,忏悔于自己的战争罪行并不断追寻两位士兵死亡的真相,坚定地反战(而不是反战败)+要求追讨天皇的战争责任,并为此实行了很多具体的行动(有些甚至也许有点偏激)。在日本这样一个普遍只反战败且对二战罪行或刻意downplay或麻木不仁的国家,这样的人还是挺难得且让我敬佩的。
无疑,摄影机跟着奥崎谦三四处活动看到了很多信息(这应该算直接电影),但由于奥崎谦三在采访其他人时频繁采取强迫/强势的逼问,导致最终得到的信息可能大打折扣(毕竟我们无法确定被奥崎谦三采访的人表达时是否因受到逼迫而伪装自己)。但如果奥崎谦三不咄咄逼人这些人又大概率会对具体内容避而不谈,所以这是个无奈的悖论。 |

|
面对不堪的真实依然躲在摄影机后静静地观望。在这样一个拒绝认罪的民族,更多的人都像山田一样生活着。从本性上,日本永远无法成为正常国家。同题材的作品已经见识不少,另一半的震撼则来自奥崎本人。谜一般的人生,让人害怕的电影。 |

|
当摄影机成为了被纪录者的工具之一,相应的,其影像资料则不仅充当了客观载体,还背负了宣传工具、攻击武器的职能。奥崎谦三使用暴力手段自然不可取,但他对战后集体对被害者采取的沉默态度的打击是有意义在的。奥崎谦三的激进让人更能从日本官方以及民间对二战历史的主流视角中察觉到自我审视与批判的重要。 |

|
原一男真的是碰到了一个十分适合“被记录”的主人公,奥崎谦三有着很强烈的表演人格,包括他一次次在摄影机前炫耀他曾向天皇射弹弓,同时又因为他的偏执和勇敢,才让日军在新几内亚上演的“人食人实录”真相大白,所以最后很难评价这样一个人,他自己总结为“暴力如果能够抵达真相也没什么不好”,只是他也付出了他应受的代价。 |

|
85/100 在现场pushing的人,与在现场pushing和backing的摄影机。电影在其中看上去是陪伴与支持的,记录戏剧化的偏执和激进,而原一男仍能让观众意识到,摄影机是更理性的。电影如果更长也许会更喜欢。 |

|
7/10。奥利弗斯通式的情感倾向纪录片,使得激进的左翼行为具有某种英雄主义的立场,片中受害者家属、县警、盘问方和摄影机一同把处刑决策者逼入室内死角,这就形成了用先礼后兵的暴力打破一切道德禁忌获取真相的人性悖论;口述朝法官小便的戏剧时刻以及高度主观性场景,对体现人物内心的变化真的有益? @2017-03-12 12:31:10 |

|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展映】纪录片往往以题材取胜。本片主角奥崎谦三就是一个奇人。二战时随日军驻扎新几内亚九死一生的他,在日本战败后勇敢地坚持声讨日本天皇战争罪行。坚定追寻战时三位士兵的死亡真相,揭开日军吃人肉的残忍事实。戳穿谎言,甚至以暴力相逼,杀人坐牢。虽略极端。但精神值得敬佩! |

|
Activist Cinema. 一方面展现了摄影机的良心,另一方面奥崎谦三对唯一真相的病态追求与军国主义同构。交谈变成搏斗的场面引人发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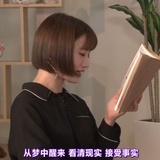
|
与其说电影导演是原一男,不如说在原一男的摄影机刺激与帮助下,奥崎谦三自导自演了一部追寻新几内亚日军于战败后23天时杀人食人真相的纪录片。这种不惜造假也要追寻真相与相对应的暧昧回答与士兵遗属的脱退就像是战后对战争责任的追问与回答一样:过去的事情翻出来有什么意义,说出真相对活着的和死去的都不好,活着的人未必能承受真相的重量。战争罪行的责任就这样在受害者(遗属)与加害者(活着的士兵,昭和)之间达成了暧昧的谅解与假装的遗忘。但是总有《岸壁の母》这样无法消散的悲哀在提醒着受害者的存在。对受访老兵的突袭就像是对每个生活在战后和平之下的观众的突袭一样,强迫他们记忆与反思。了解了一下奥崎谦三,原来他看到自民派阀“木曜会”忘年会新闻之后,就准备杀田中角荣了。昭和生日那天,右翼宣传车和他的宣传车出现在同一镜头中。 |

|
摄影机时不时显露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暗示着奥崎谦三未必是表面上那样一个斗士,也不完全是一个揭露真相的引导者,他同时也是事件之外的被摄主体,但是观众却几乎看不到他的生活,因为他根本没有生活,他是经过战争摧毁后被历史遗留下的幽灵,不断地侵入当下的现实世界,其间侵略者的行为方式和受害者的良知正义扭曲在一起发生冲撞。奥崎谦三实际上和所有受到追问的当事人一样,其存在就是作者之于历史的一种控诉,只是后遗症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又使他成为了影片表达结构上的联结。 |

|
探索纪录片伦理边界的电影。导演全程目睹了奥崎的(当然是具有正义性的)暴力调查行动,甚至让摄影机起到了背书、让奥崎起到了事实上联合创作本片的作用。但是,据说当奥崎在最后邀请原一男去拍摄他最后针对上尉的刺杀行动时,原一男选择了拒绝(但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奥崎和当年战友长官们不断反复探讨新几内亚发生的事的谈话引发了观影者巨大的遐想空间。我个人则总是忘不了他的妻子:这个笑眯眯的微胖妇人默默陪伴乖戾嚣张的奥崎进行他的战斗,全程不发一言,在奥崎入狱后终于占据了镜头的中心位置,但紧接着字幕就宣告了她的死亡。 |

|
9.0/10。前二战士兵奥崎谦三,不断采访当事人追问两士兵被害真相的故事。奥崎谦三是反战人士,二战在新几内亚,战后声讨天皇并曾弹弓攻击天皇,多次入狱,并认为合适的时候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阻止更大的暴力,小的暴力是非常必要的,挥舞着他那没有小拇指的左手,也sha ren坐牢,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人。一次次拜访艰难拼凑可怕真相:关于食人、绝望、战争和人性。 |

|
8.5的豆瓣评分个人认为是低估了,这部纪录片看起来不像近年来大热的这些片子那样“精致”最大的原因是原一男将导演的主导权有意识地过渡给奥谦,这使得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奥谦在追问战争罪人时更加咄咄逼人,但无形中也是一种事件引导,这种手法其实并不那么属于原一男,也许里面还掺杂了今村昌平的意愿。但无论如何奥谦的行径看似执拗乖张,但极端战争环境下的过来人可以舍掉一生去找寻最终答案,这一点真实还是颇为让人侧目的,他不是纯粹的偏执,相对于吃人的荒唐,奥谦已经是无比克制讲理了,只要承认罪过讲出事实真心悔过,他也并不穷追不舍。也难怪今村看不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样的片子对比起现实简直就是美化战争的浪漫爱情剧…… |

|
原一男实际上借助影像和戏剧性消解了奥崎谦三身上的不少戾气,很难知晓经过影片的压制损失了多少原始的情绪(像片中打人的场景丝毫不能让人感受主角身上的反骨),也很难想象一个人在摄影机前不会产生自我感动式的表演,但精彩之处在于,这并没有淡化抗争的力量,反而使狂热与沉静相互抗衡,缓缓触及日本的民族病灶,应该说本片没有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奥崎谦三,但呈现了战时和战后日本社会的两种病态。 |

|
奥崎谦三,二战时驻新几内亚,其战友八成战死。昭和31年,他打死一个地产商,坐牢十年。昭和44年,他用自制弹弓子射天皇,坐牢一年半。昭和51年,涂鸦天皇画像,坐牢一年零2个月。昭和56年,因筹划刺杀前内阁总理被捕,未被起诉。这部记录片里,他在追问当年军官下令吃士兵的肉的真相。就是这样。 |

|
很震撼的紀錄片,徹底的戰爭反省。二戰在南洋倖存的日本兵奧崎謙三,超獨特但也很難拍。導演與被攝者的"紀錄片格鬥技"由此展開,旁人說奧崎瘋狂,或許吧,但重點上頭腦無比清晰,難忘他揮舞著殘缺手掌疾呼的模樣,片尾配上了太鼓聲,彷彿這奇人執拗的力量持續重擊觀者,逮著機會在大銀幕連看兩次滿足了 |

|
企画 今村昌平
第一部原一男,强大而有力量的意志力与勇气支撑起了一个固执的人,叫神军而不是皇军是因为坚信在天皇之上依旧有一位自由平等的神,并为推翻统治和揭露战争事实(实现个人理想/欲望)而永不停止斗争,跟随摄像机进入他的世界后感受其的情绪,愤怒,暴力与反抗。三角关系的变化与对峙,画面内对拍摄者的指示,导演个人的立场体现(甚至出现在对面),记录着暴力的同时仿佛也在行使暴力,“如果是能为人类带来好处的暴力,是可以被原谅的”,那份永不放弃坚定自我的神军精神永远值得钦佩。 |

|
受害者为难受害者,没有比从根本上不能相互理解的人硬要坐下来谈更可怕的事。奥崎谦三把自己当新世界的神了。有些对他经历有猎奇心态的人,对他事实上的暴力产生认同感,跟对战争暴力产生认同感有何区别 | 虽然是今村昌平企划,他的影响不怎么明显 |

|
几乎全程在爆笑和愤怒两种都很强烈的情绪中不断切换。无论是从个人经历还是历史观察中,我都相当确定的一个事实是,记忆是可以被时间和主观意识篡改的,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过去事实的存在状态,除非在一定时间期限内,有人像奥崎谦三这样,坚持不懈地通过交叉验证,找回遗失的拼图,还原真相。转念一想,又近40年过去,人们得到的是哥斯拉-1.0这样的献礼片,回答已经明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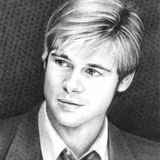
|
翻译严重有问题,我居然把男猪脚看成了好战份子,原来他是揭露日军罪行的,不过看这样的片子更加深了我对鬼子的厌恶 |

|
1987年奥崎谦三被捕,同年该片制作完成上映,就如片中奥崎谦三一直强调的神的意志,他最终的活动让这片犹如获得了神的助力一般终得以完成,并使之与其他纪录片分别开来,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境界。 |

|
可以和《飘舞的军旗下》搭配着看,然后会发现剧情片哪怕再有冲击力,一碰上纪录片,还是设想得过于天真。《前进,神军》里被访问对象的态度正说明了日本政府以及参与者对罪责的态度,不可能再去回忆,不可能会有真相。 |

|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标记这部想看的契机是什么了,但可能今天不看又要等好多年。选这个角度切入作为反战(?)题材,就算光是复述这个故事都会不明觉厉。要不是因为化了眼妆强忍着不去哭,我真的觉得太沉重…比吃人更痛苦的是将吃人作为秘密维护了那么多年吧。有些看起来真的太过戏剧化的反而更真实吧 |

|
“暴力是我的强项”, 蹲了13年监狱,思路清晰,意志坚定,有礼有节, 军事法庭需要这样打闪电战的雄辩家。战争亲历者居然还残存有福音教派的顽强传教体质,敬畏他在悲痛中不卑不亢的控诉,不像那些再也抬不起头来而苟活的人。 |

|
极有表演欲的偏执狂,碰上同样偏执狂的摄影兼导演,这种镜头的存在感在其他纪录片电影中是不多见的。而且可以看到在演员不配合的情况下,导演是如何重新整理素材让整个电影更有条理,尤其是这种抽丝剥茧般的去还原事件真相,原一男导演在这部纪录片里体现的素材整合能力,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 |

|
震撼而深刻的作品,用参与模式(奥崎既是被摄者,又是采访者)挖掘历史,执着寻访真相者与刻意遮蔽事实者构成全片最大的冲突,虽然未必获得完全的真相,但镜头前的一切(回避、抗拒、坦承、忏悔)也是吸引力十足的真实。对被动执行的平庸之恶的揭示发人深省。同样值得深思的是,当刚烈暴戾的奥崎信奉为了人类美好的正当目的可以行使暴力(包括假扮受害者亲属)时,他是否离他所痛恨的不择手段的战争狂人(也即昔日的自己和他的同袍)不远呢? |

|
个人很爱这部电影,纪录片。其实直到中段,都觉着他是不是有点过分执拗咯,可是看着看着,渐渐理解嘞,尤其是他在其中某位的家中两人爆发强烈的争吵甚至肢体冲突使对方报警,在不断地逼问与自我阐述忏悔中,对他肃然起敬。不是所有人、或者说很少人才会有这样的感悟与深刻的反省。既然是罪,就得还。 |

|
开始半小时看着就哦一个神经病hohoho,也没咋关注他在说啥(字幕也不好,听力又差)。。然后看着看着就黑猪(新几内亚当地人)白猪(盟军俘虏和日军士兵)了。。?最终不同人被逼出的“真相”仍然是不尽相同,有人说是先吃黑猪,也有人说不习惯当地人,还是吃自己人,为了不一起饿死,就杀掉一个吃,吃的时候也会恐惧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追究真相的奥崎谦三是一个极度的偏执狂,为了自己心目中神的正义,不惜犯罪不惜杀人,但没有这样的人也可能真的永远逼不出真相。。片子另一个看点是,80年代日本人的礼貌,包括偏执狂奥崎谦三在内的这些前日军老兵,很可能还是吃过自己战友的老兵,在如此终极的逼问和被逼问之间大多数时候还是保持着日式礼貌,哪怕一言不合扭打起来,事后也继续平和地不停互相鞠躬。。这些奇特的组合非常令人叹为观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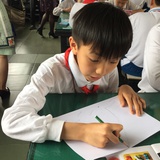
|
导演和被摄者在态度与气质上达到的高度统一,把这种愤怒、偏激乃至疯狂展露无遗。从影片开始时让人思考事件本身,到后来更多的聚焦于主角,对暴力的正当性与正义进行思考,再到这般悲壮结尾,真是让人起敬 |

|
据Hara桑说,有三段重要剧情都是谦三安排的,其中一个是餐厅说要做生意那段,Hara桑拍的时候都不知情。 |
![豆瓣评分]() 8.7 (1234票)
8.7 (1234票)
![IMDB评分]() 8.2 (2,060票)
8.2 (2,060票)![烂番茄新鲜度]() 烂番茄: 100%
烂番茄: 100%![TMDB评分]() 7.34 (热度:2.45)
7.34 (热度:2.45)























































